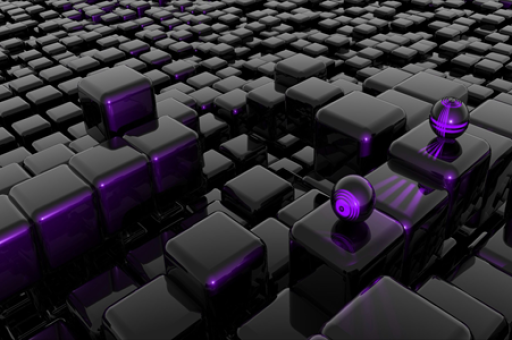从“杭州六小龙”看民营化和市场化的新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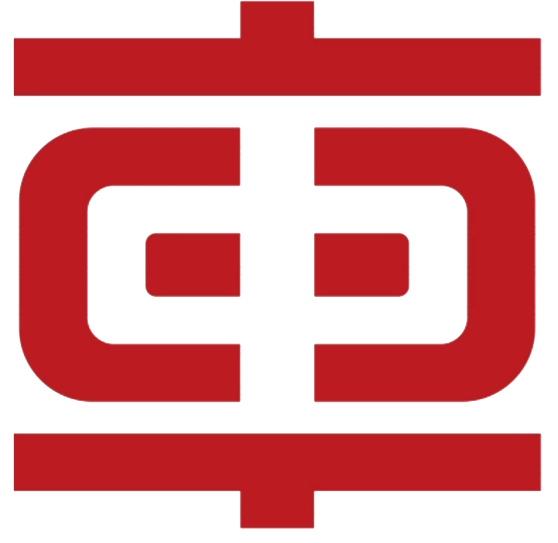 摘要:
编者按:在全球科技竞争与城市转型的背景下,如何构建有活力的创新生态,成为众多城市面临的共同课题。杭州,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策源地,其探索不仅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样本,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
摘要:
编者按:在全球科技竞争与城市转型的背景下,如何构建有活力的创新生态,成为众多城市面临的共同课题。杭州,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策源地,其探索不仅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样本,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 编者按:
在全球科技竞争与城市转型的背景下,如何构建有活力的创新生态,成为众多城市面临的共同课题。杭州,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策源地,其探索不仅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样本,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大国创新提供了观察窗口和实践参考。
5月18日,中信出版集团联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办《科创与中国》新书分享会,邀请学者、投资人等共同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范式,通过回溯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路径探寻发展前景的多种可能性。
以下为本次活动嘉宾、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所作的演讲整理稿。
为什么“浙江模式”是用改革推动发展?
今天,我与大家交流浙江模式与新质生产力和“杭州六小龙”的崛起。这个演讲的第一个关键词之一就是“浙江模式”,那么,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何为“浙江模式”?然后,我们再来谈谈,在“浙江模式”下新质生产力何以得到释放和发展,为什么“六小龙”可以在浙江杭州这样的一片热土上诞生?
我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就考了研究生,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到杭州来教书,至今已经40多年了。我来杭州后参加的第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就是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暨2000年的远景规划研究。目前,我还担任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参与浙江省“十五五”规划研究,这是我参与的第九个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所以,我对浙江的经济发展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省的GDP总量约为130亿元,在当时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14位。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后,去年浙江的GDP已达到9万多亿元,全国排名第4,仅次于广东、江苏和山东。由此可见,浙江的经济发展非常快。
1998—1999年,我承担了两个重要课题:温州模式研究和浙江现代化道路研究。这两个课题后来都有著作出版,一本是《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另一本是《浙江的现代化道路:1978—1998年》,在这两本书中,我们提出了一个研究浙江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框架,回答什么是“浙江模式”的问题。
众所周知,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切入,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
一方面,经济发展可以表现为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时,资源配置活动通常大都在初级产业部门,比如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矿业等,这些产业部门是人通过使用工具直接与自然打交道来获取产品。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配置会从初级产业部门向更高级的经济部门转移,先会转移到制造业和建筑业,即现在所说的第二产业。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源会继续转移到服务业及现代服务业,即通常讲的第三产业。因此,资源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这些产业部门中不断流动和优化配置,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通常讲的“工业化”。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同样可以表现为资源在不同空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经济发展落后时,资源配置分散在广大的农村区域;随着经济发展,资源不断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及中心城市流动,向具有区位优势的空间聚集和配置,这一过程就是经济学通常说的“城市化”。
从经济学资源配置视角看,地区经济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工业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城市化。接下来的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如何启动的?如何推动的?为什么浙江能迅速启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同样,从经济学资源配置的视角看,启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动力来自资源配置主体的变革。谁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在浙江,改革开放前资源配置的主体是谁呢?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包括农村的人民公社,我本人1975年高中毕业到农村插队,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参加过三年集体劳动。
改革开放后,资源配置主体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大量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民营企业蓬勃发展起来,取代了原先单一公有制经济组织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资源配置主体的变化就是“民营化”。
另一方面,动力来自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用什么方式来配置资源?改革开放前,我们是计划经济,主要用计划的方式来配置资源。改革开放后,浙江这样的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了,是因为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变化。资源配置方式从以计划经济的计划为主转变为以市场经济的市场为主,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就是“市场化”。
至此,我们的答案已经明确了。什么是“浙江模式”?“浙江模式”就是用民营化和市场化去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模式,既是制度变迁的模式,也是经济发展的模式。
民营化和市场化是什么?是改革,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什么?是发展。因此,“浙江模式”就是用改革推动发展的模式。
为什么“浙江模式”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回答“浙江模式”与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讲得很清楚,生产力有三个要素,第一个是劳动者,第二个是生产工具或者叫生产资料,第三个是生产对象,即劳动的对象。生产力为什么能得到较好发展,一定是有能适应它的生产关系。有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就可以解放生产力、释放生产力、提高生产力。
实际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及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关系,跟前面讲的改革和发展的关系,道理完全相同。民营化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生产关系。
第一,为什么民营化很重要?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民营化就是社会经济制度中的“自由企业制度”,其本质是给予老百姓在资源配置活动中的自由选择权利,即老百姓有权自主从事资源配置活动,且这种权利是在国家法律法规保护的范围内是可以自由行使的,例如我们国家出台的《民营经济促进法》。
自由企业制度赋予老百姓自由从事资源配置活动的权利,这句话包含几层含义。
首先,老百姓的经济活动是可以自行决策的。原来我们在农村插队,在生产队干活,劳动力是束缚在集体经济组织上的,不是完全自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民的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可以自主决定种什么、何时种,以及除土地耕种之外从事其他农副业活动。这样一来,劳动力就解放出来了,在资源配置活动中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自行决策。
其次,自由企业制度中的经济主体所做的决策及相应的投入,都是需要自己来承担责任的,成本不能随便转嫁给他人。同样,自由企业制度中,如果投入成功产生收益,这个收益是归做出决策和承担成本的经济主体的。经济主体需要为自己的投入和产出负责,投入和产出应该内部化,不能外部化。
这样的自由企业制度,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有力且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人们从事资源配置活动。
第二,为什么市场化很重要?市场化即自由交易制度。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市场发展会促进社会分工,交易越发达,分工越细致、越发达,产品越多样化,生产技能、技术进步就越快。交易和分工是相互促进的。从浙江的实践中我们都看到,自由交易制度可以促进社会分工、提高生产力,提升经济效率。
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关键的两个词——激励和效率,在民营化和市场化中都体现了。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浙江模式”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包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它背后有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和效率提升机制。
为什么“六小龙”出现在杭州的原因?
浙江的民营化+市场化推动工业化+城市化的模式,这种具有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效率机制的模式,为什么最终在杭州成就了“杭州六小龙”?
首先,“六小龙”之所以出现在杭州,是因为这片热土拥有民营经济和市场化激励了老百姓的创业和创新,促进了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的互动。
新世纪初,杭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工业化从中期开始向后期转换。改革开放之初的工业化以农村工业化为主,生产的产品以满足人们的日常消费需求为主,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传统消费品。到了本世纪初,杭州的工业化就要升级了,但发展的方向是有争议的。我们能否不走从轻到重的传统工业化老路?
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其间提出“八八战略”,提出了新型工业化,提出了新型城市化。
那么,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如何互动?在杭州,推动新型城市化不仅是工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也是城市化自身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资源配置的最佳空间不在大城市,而在县域,因为以农村工业化为主的工业化,其产业发展、劳动力、原材料、商品销售等都以县域经济为载体。随着工业化从中期向后期转变,城市化向新型城市化发展,浙江省和杭州市改变了经济发展的空间战略,从强县战略转到都市区战略,即发展大城市。
杭州先是将萧山的三个镇划进杭州,变成滨江区,随后萧山、余杭、富阳、临安等也相继划入。城市扩大了,城市布局舒展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了,发展环境也随之改进,这样新型城市化就产生了吸引高端生产要素的吸引力。
大量新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大量的人才,包括国内外的创业创新人才来到杭州。本世纪初,杭州最有代表性的两家企业,分别是制造业的UT斯达康和服务业的阿里巴巴,一个靠“硬件”,生产“小灵通”手机;一个靠“软件”,发展电子商务平台。
高新科技人才集聚和新经济产业发展,使整个杭州成为一座互联网+创业城市。十几年前制定杭州发展规划时,我曾建议杭州要大力“培育‘互联网+’国际领袖企业,打造‘互联网+’国际创新城市”。如今,我们可以把“互联网+”改为“AI+”。
今天我想说的是,浙大系、阿里系、海归系、浙商系的背后,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即杭州的投资机构,那些VC、PE等民间的投资者。由于经济发展存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二元结构,许多产业的上游和通讯、金融等行业大多由国企控制,民营企业资本难以进入。但是,在许多新经济领域,如互联网+、AI等,都是新兴事物,民营经济的投资和发展反而都“被逼”集中在这些产业领域。这些民间投资机构的崛起,不仅推动了互联网+、AI等领域的创业创新,还延续了浙商从改革开放初就有的敢闯敢干和勇立潮头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新的时代又重新焕发出来,成为杭州创业创新的巨大力量,造就了“杭州六小龙”的涌现。
“杭州六小龙”的出现,与城市化和工业化及城市与产业的互动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它们背后体现了一种新的民营化和市场化的路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需要依靠民营经济这支重要的力量,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事关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事关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也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
(作者史晋川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本文为作者在“破解科创密码 展望经济发展”暨《科创与中国》新书讨论会上所作的演讲整理稿,经作者本人审订。《科创与中国》一书,2025年5月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作者:访客本文地址:https://www.zsclv.com/zsclv/11222.html发布于 2025-05-27 10:34:08
文章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处中首车旅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