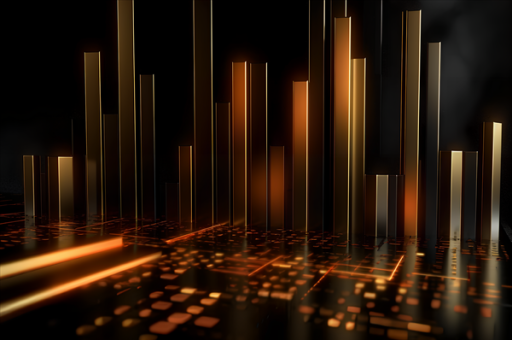东风从西边吹到了长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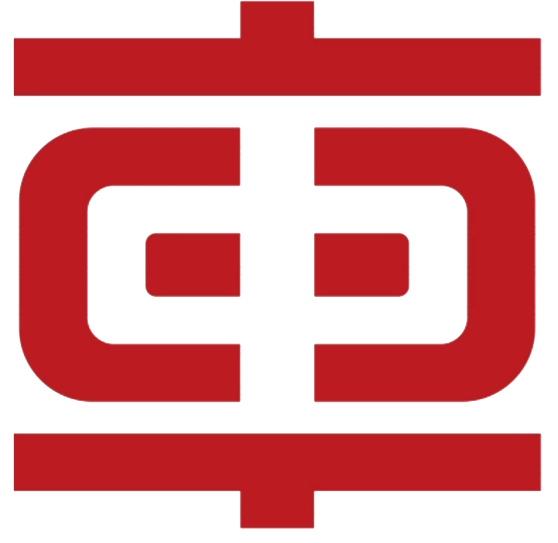 摘要:
六十一年前,原田伴彦在《长崎》这本书的序文中用很文学的笔调煽情地写道:长崎,是一座飘荡着清澄的忧愁的城市。到长崎来旅行的人,在那里会感到一抹哀愁的同时,一定也会注意到那里存在着使人...
摘要:
六十一年前,原田伴彦在《长崎》这本书的序文中用很文学的笔调煽情地写道:长崎,是一座飘荡着清澄的忧愁的城市。到长崎来旅行的人,在那里会感到一抹哀愁的同时,一定也会注意到那里存在着使人... 六十一年前,原田伴彦在《长崎》这本书的序文中用很文学的笔调煽情地写道:
长崎,是一座飘荡着清澄的忧愁的城市。到长崎来旅行的人,在那里会感到一抹哀愁的同时,一定也会注意到那里存在着使人产生神秘愉悦的某些物象。长崎是一座酝酿出奇异的哀欢芳香的城市。(《長崎:歴史の旅への招待》,中央公论社1964年,第1页)
长崎,我只是短暂地去过两次,完全只是一个匆匆的旅人。但去之前,已阅读过一些文献,在那里又有了一些实际的体验,对我而言,与其说是文学的长崎感动了我(这一面肯定有),不如说是与异域的文化交杂融汇后产生出的独特的历史氛围更令我感到兴奋。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后期的三百余年中,来自东亚大陆和遥远的欧风美雨,同时都在这里(包含了今天长崎县的平户)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就这一点而言,整个日本列岛,可谓无出其右。
从“唐人屋敷”到新地中华街
16世纪20年代西班牙人麦哲伦的团队完成了人类首次的环球航行后,东西大两洋之间,才真正开始了人与物的直接交流。耶稣会基督教的东传,逐渐改变了东亚的局势,也将长崎(平户)抬升到了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即便是与传统的中国的往来,也染上了新的色彩。
17世纪初,福建泉州出身的海商李旦,在明朝海禁和开禁的空间,先是出海南洋,在马尼拉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后来移往平户(平户和长崎都属于当时的肥前国松浦郡),以此为据点,从日本幕府那里获得了允许进行海外贸易的朱印状,创建了一支由12艘商船组成的船队,来往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1625年李旦死后,也是泉州出身的郑芝龙成了新的首领。郑芝龙少年时父亲去世,去澳门投奔舅父,在那里信奉了天主教,他的洋名是Nicholas Iquan(后者可写成汉字“一官”),1621年加入李旦的旗下,移居平户,得到平户藩主松浦隆信的宠信,与平户藩士田川七左卫门的女儿松(有中文文献称是旅居平户的福建人翁翊皇的养女)结婚,郑成功便是两人的儿子(幼名田川福松),七岁时随父亲回到福建。长大后继承父业,成了在台湾赶走荷兰人、力图抗清复明的英雄。明亡后,明皇族的后裔朱聿键(南明的隆武帝)对谒见他的郑成功,赐予国姓“朱”,郑虽然一直没有使用,但“国姓爷”的称呼却在民间传开,1715年日本的净琉璃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写过一部以郑成功的事迹为题材的名作《国姓爷合战》。由此可知,17世纪前期的二十来年中,李旦、郑芝龙等中国海商的商船已经频频进出平户港,且有一个时期,一直居住在平户。17世纪初前后,从丰臣秀吉至德川幕府,日本对西洋诸国,逐渐实施锁国,但对中国的商船,并不严禁。
据生卒于长崎的西川如见(1648-1724)印行于1719年的《长崎夜话草》记载,唐船在1562年,初次进入了长崎境内的户町(不是今天的长崎港)。1570年,肥前国大名大村纯忠辟建长崎港(有关长崎地名的由来,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翌年葡萄牙商船入港,之后,长崎港逐渐崛起,受到海外贸易商的青睐,其地位最后超越了平户。1635年,幕府规定中国商船只可从长崎进入,于是,长崎成了中国人的新的集聚地。 由于明清两代长期实施海禁政策,中国人难以直接从大陆本土渡海前往日本,很多都是迂回从海峡对岸的台湾和东南亚诸国来到日本的。
据文献记录,在1634年以后的十年内,每年大约平均有57艘商船自中国来到长崎,每艘船平均大约有船员50人左右,这一数字随着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的变化有所增减。一开始中国人是可以随便居住在日本人开的民宿或简易客栈内的,这也激活了当地的青楼业,形成了江户时代日本三大青楼街之一的“丸山游廓”。在郑成功后人的抗清武装不得不接受朝廷的招安之后的1684年,清廷撤除了“边界令”,允许沿海民众出海与日本做贸易,于是来到长崎的商人数量剧增,为了减少中国船员与当地人之间的纠纷,1688年长崎奉行所在长崎郊外的十善寺乡(现为长崎市馆内町)着手兴建“唐人屋敷”,费用来自长崎的商人向幕府的借款,翌年完工。听起来唐人屋敷有点类似今天的唐人街。不过“唐人屋敷”是被封闭起来的,外面建有一条水濠,再用围墙和竹篱与外界相隔,一般人不得随意进出,但是青楼女子和僧侣可以进入。据文献记载,“唐人屋敷”共有三万六千多平米的面积,里边除了仓库货栈等之外,大约有20栋两层楼的房子供商人和船员居住,由于当时往来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海上航行相当不易,一般人会在此平均居住180天左右。由于1698年的一场大火,把五岛町等的中国商船货物的仓库烧毁了,于是就在唐人屋敷所面对的海上填海造地,重建仓库,这里就被称为“新地”。1784年,唐人屋敷遭遇大火,除了里面的关帝堂还留存外,其他全被烧毁了,此后整体就再也没有重建,于是日本当局就允许中国人自己建造居住的房屋。唐人屋敷一带,除了今天特意竖立的一块“唐人屋敷通(通,这里是路或街的意思)”的路标之外,几乎已没有什么痕迹了。好在当年日本的画家曾留下了一些描绘唐人屋敷的绘卷,可以一窥当年中国人在此地的生活实景,除了日常居住的房屋外,还建造了关帝堂和妈祖庙。当时,日本人延续了自奈良中期开始的肉食禁令,日常食物中消失了肉食的香味,但中国人在唐人屋敷内,养猪养鸡,大抵过着与本土无异的生活。
当时中国的船只主要来自福建和浙江一带,带来的货物主要有生丝、纺织品和砂糖,其他还有皮革、中药和书籍等。商人们运送书籍,首要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传播文化,而是中国的书籍在日本拥有广泛的市场,可以盈利,这一时期传入的书籍主要有中国的古典、文学书、历史书、医学书、本草书等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就是通过这一途径传入日本的,它对江户时期的通俗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或人员往来,到了19世纪中期,已呈强弩之末的势态,鸦片战争以后国势的迅速衰败,以及太平天国引起的剧烈的内乱,严重削弱了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从1844年到1858年间,驶往日本的商船,每年不满十艘,到了后期,只有孤零零的一艘了,1858年,最后的一艘唐船,成了绝尘的风景。就在这一年,幕府与英法美俄荷兰五国签署了通商条约,日本向西方,正式打开了大门,长崎,则是五个对外开放的港市之一,当局为陆续到来的西洋人,开辟了一块外国人居留地,免费租借给欧美人,供其建屋和营生之用(不同于中国的租界,长崎的居留地在1876年归还给了日本)。西洋人成了新时代的宠儿,残留在长崎的中国人,一时陷入了囧困的境地。少数富有的华人,成了洋人的附庸,寄居在外国人居留地,少部分人辗转回国,潦倒穷困者,则蜗居在唐人屋敷残迹中的破屋里。1870年1月17日,一场大火,把唐人屋敷最后的一点破屋,也完全烧尽了。在同济大学开会时曾有几次晤面的横山宏章教授说:“以此为契机,所谓的唐人社会消灭了,华侨社会出现了。”(《長崎唐人屋敷の謎》,东京集英社,2011年,第207页)确实,更多的华人,则在填海造地后拓建的用于建造货物仓库的新地,开辟自己新的生存空间,这就是今天长崎新地中华街的由来。
那天从出岛出来,移步西南,几百米之外,就是今天的新地中华街,大致是一个四方形的街区,东西南北,各有一个门,分别寓意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北边的玄武门,算是正门(一般以南边的朱雀门为正门吧),一条有点海水味的小河上,筑有新地桥(桥的栏杆漆成了中国风的朱红色,日本多为橘红色),桥的南侧,有一门楼,黄瓦赤柱,色彩艳艳的,上面几个端正的“长崎新地中华街”的字,是1986年建造时,由当时的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王震(后担任了国家副主席)书写的。日本所谓的中华街,差不多就是中国美食街的代名词了,现在与横滨的中华街、神户的南京町并列为日本三大中华街,横滨和神户,是后来开埠的,在对外交流上,长崎倒是长兄了。新地的中华街,主街只是一条巷子而已,汇聚了诸如王鹤、京华园、会乐园、江山楼等二三十家中餐馆,也是艳艳的招牌,大一些的店,门口的两个石狮子,几乎也成了标配。我到的时候,已是下午三点多,据说平日门市的生意一直不坏,中国菜的魅力,一般人很难抗拒。
中华街的东南侧,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公园,曰“湊公园”,近年兴建的,有一个明清风格的中华门楼,一边是粉墙黛瓦的墙垣,有几处中国风的绿植小品,也有一处短短的廊阁,可供人小憩,规模小于冲绳那霸的“福州园”,似乎与中华街遥相呼应,在东洋异域,营造出了一点中国的风韵。
长崎的华人,来自中国沿海各地,以福建人居多,福州、福清、漳州、泉州、厦门都有,日本在对西洋开放后,面对西洋的优势,华人依旧殚精竭虑、筚路蓝缕,顽强地坚守乃至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到了1870年前后,华人在长崎一带的势力得到了稳固和发展,人数也在渐趋增长,出于浓厚的乡土情结,居住在长崎的福建人于1868年创建了凝聚乡情的八闽会馆(1897年改建为福建会馆),1870年代,出身粤地和闽地的华人分别成立了广东会所和三江会所。
会所的旧迹后来逐渐湮灭,福建会馆仍有部分留存,2007年初春我曾去踏访,位于馆内町一丁目,建在一处小小的台地上,沿石阶往上走,仰首可见一门楼,宋代风格,端庄秀丽,有“福建会馆”的匾额,入门有一前院,正面是正堂,堂前的匾上书写三个字“星聚堂”,堂内金色底面的匾上写有“桑梓万里”四个字。据说会馆的正殿已在原爆中毁坏,现在的门楼和正堂的柱子,看上去也是新构。正堂的右面,竖有一尊小小的(其实是等身大)孙中山的一手插裤袋、一手拄手杖的铜像,这自然是后来塑造的。未见其他的房屋,大概都在后来圮坏了。
在今天的长崎,最具中华风的,应该是每年一度的中华提灯节了。其实历史并不很悠久,缘起于1986年新地中华街牌楼的建成,由民间的中华街振兴组合倡议发起,从翌年的1987年春节开始,年年定期举行,结果人气节节爆满,长崎市政府也借机将它列入都市发展战略的一环,在各方面给予大力的推动,成为正式的观光支柱,不仅只是五彩斑斓的灯笼,还伴以中国的舞狮舞龙,配以迷幻的灯光和彩妆艺术,以“长崎鲜活的异国CHINA再发现”为理念,搞得风生水起,届时一万五千盏中国灯同时亮起,声光影电交相辉映,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大量的观光客,2018年,年仅二十岁的长崎出身的人气女优长滨ねる(汉字或许勉强可写作“练”)以及她所在的演唱组合“樱坂46”也加盟这一提灯节,更加推高了原本就很炽热的人气,成了目前长崎最炙热的一张名片。
对于长崎而言,洋风,不仅可以是西洋的,也可以是东洋的。
“三福寺”、隐元和孔子庙
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根脉足够深厚,当这一民族的成员移居海外后,一定会建造物理上的有形物来传承自己的文化根脉,并从中寻求自己的文化定位和精神慰藉。对于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而言,儒道释,大概就是自己的文化根脉了。
17世纪前期,移居长崎的中国人逐年增加,年长去世了,受大海的阻隔,未必都能埋骨故土。像欧阳华宇等比较著名的人士,就埋葬在长崎奉行(“奉行”,官职名,大抵类似今天的长崎市长)小笠原一庵(原本在京都出家的僧人)于1598年创建的悟真寺(真言宗)的墓地内。之后,在长崎代官(“代官”,官职名,后来大抵改为“奉行”)末次平藏的助力下,中国人的墓地大致修整起来了。但是,去世的人,仅有葬身之地,似乎还不够,总要做些亡灵超度的佛事。进入江户时代后,幕府施行了一种“寺请证文”制度,就是民众都要向附近的寺院去办理一个证明自己不是基督教徒的手续。日本的寺院,长期以来形成了所谓的“檀家制度”或是“寺檀制度”,即各个寺院有相对固定的檀家(信奉佛教的施主),檀家向自己的菩提寺进行布施和供养,寺院则向檀家提供丧葬和佛事的便利。中国人到了日本,难免会有“客家”的感觉,无法完全融入日本的“寺檀制度”,再加上之前的悟真寺属于真言宗(空海在806年自唐归来后创建的宗派),对于移居长崎的沿海中国人多少有些违和感。沿海的中国人,尤其是福建一带的航海人,一直有妈祖的信仰,内心祈求和相信妈祖能保佑海上的太平,因此,差不多每一艘船上,都放置了妈祖的神像,他们希望常去参拜的寺院内,能有妈祖像,于是就计划在长崎创建中国人自己的寺院。
来往于长崎的中国海商,通过贸易积累了一些财富,他们能够出资来建造自己的寺院,长崎当局对此也惠予支持。但是,寺院内必须要有具有资格的佛僧,要有开山者。1624年,江西浮梁出身的真圆(俗名刘觉)利用富商欧阳华宇在寺町的一处宅邸,创建了全日本由中国人建造的第一座佛寺兴福寺(俗称南京寺,因明最初在南京建都,日本与中国的勘合贸易始于首都尚在南京的明王朝,后来日本就将来到日本的中国人,泛称为南京人)。刘觉是1620年来到日本的海商,四年后出家为僧,在当地华人的捐助下,创建了后来隶属黄檗宗的兴福寺,并安置了妈祖像。该寺现在已被列为日本的国家重要文化财(大略相当于中国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一年后,真圆隐退,将住持的法席禅让给了1632年携带了明版《大藏经》来到长崎的出身江西九江的禅僧默子如定。如定精通镶嵌工艺,又擅长书法,将相对先进的中国文明带到了长崎。默子还是留存至今的长崎市内著名的眼镜桥建造的发起人,在中日两国工匠的努力下,建成了日本第一座石建拱桥,为了纪念他的功绩,1994年,在桥的左岸广场上,竖立起了默子的铜像。1645年,默子隐退于东庐庵,将住持禅让给了逸然性融。兴福寺内现存的大雄宝殿,为重檐歇山顶建筑,上一层仿宋代风格,下一层为舒展的明代风格,略如后来隐元和尚在京都宇治创建的黄檗山万福寺主殿。
居住在长崎的华人,以福建出身的居多。1628年,泉州出身的僧人觉海在弟子了然和觉意的陪伴下来到了长崎,在原岩乡(现筑后町)结庵,供奉海上守护神天后圣母(妈祖),1649年,在泉州开元寺出家为僧的蕴谦戒琬受长崎的泉州籍居民的邀请,来到长崎,在华人的捐资下,在觉海初创的僧庵地,兴建了后来也隶属于黄檗宗的福济寺。1655年,曾师从隐元的开元寺僧人木庵性瑫受先一年抵日的隐元的召请,来到长崎,担任了福济寺的住持。因而该寺被称为泉州寺或漳州寺。1910年,该寺的大雄宝殿、青莲殿等被列为日本原来的国宝(相当于现在的国家重要文化财),可惜在1945年的原子弹爆炸中被炸毁。1979年,为纪念在原爆和战争中的死难者,在原来大雄宝殿的遗迹上,建造了万国灵庙长崎观音,很可惜,昔日的旧貌,已不可追寻了。
在长崎的三座或四座唐寺中,我最感兴趣的要数崇福寺了。虽然同为福建人,但福州与南部的泉州、漳州语言并不通,长崎的福州居民觉得也应该建一座福州人的菩提寺,就在1629年请来了福州出身的已年届六十三岁的僧人超然,经过一番筹措准备,于1635年建成了崇福寺,纯然的明代风格,且完全是中国式的寺院。日本式和中国式寺院的一个较大的区别,就是日本的寺院在上台阶(台阶都是木造的)时,就必须脱鞋,整个寺院的堂内及檐廊的地面,均为木造,日常擦洗得十分干净,可随时席地而坐,堂内多半是榻榻米。而中国式寺院,台阶一般为石阶,地面也是石块铺设,里外均无需脱鞋。纯然中国风的寺院,长崎的崇福寺大概是第一座。寺内还有关帝堂、妈祖门,明显染上了闵地的色彩。这里不仅只是一座寺院,还成了一所教育机构,下文要讲到的唐通事,就曾在寺内开设译家学校,日本打开国门后,早期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威廉姆斯(Channing Moore Williams),来到长崎后,鼓励他的门生瓜生寅在崇福寺内的广福庵开设了英语学校“培社”,威廉姆斯后来又是东京的教会大学立教大学的创办人,“培社”也就成了立教大学的源流之一了。如此说来,崇福寺就不只是一座禅寺,还与教育紧紧连在了一起。如今,当年建造的大雄宝殿、第一峰门等,都被列入了日本的国宝,其他的大部分建筑,也属于国家重要文化财。
开始时,长崎三福寺,都属于禅宗的临济宗或曹洞宗,兴福寺的第三代住持逸然,希望将黄檗宗也带到日本来,就想请福清的万福寺主持隐元隆琦请来,接任崇福寺将要隐退的百拙住持,并就此事,与当时逗留在兴福寺的无心进行了商议,无心一开始推举了隐元的弟子也嬾性圭。受到召请的也嬾,在1651年面会了隐元,然后从厦门出海启程前往长崎,不意遭遇海难身亡。于是逸然请人三次渡海向隐元发去了邀请函,不意有前两次遭遇海盗,书函与其他物品都被海盗抢夺,第三次的书函送到了隐元的手中。于是隐元就先后派了良者性光、木庵性瑫等前往长崎,了解当地的实况。隐元在接到了他们的报告后,就决定启程前往日本。1654年旧历六月二十一日,隐元总共率领了五十余人,从厦门出发,七月五日抵达长崎,今天的兴福寺内,还留有隐元当初挥毫书写的苍浑遒劲的“初登宝地”的墨迹。
不过隐元没有在长崎久居,一开始,京都的妙心寺想请他去做主持,结果没有成功,他被邀请到了今天大阪府高槻市的普门寺,1658年又去江户会见了江户幕府的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此后在日本朝野的资助下,在京都宇治开建了黄檗山万福寺,今天的宇治川岸边,建有隐元登岸纪念碑,我曾于2010年和2024年两次去踏访,在拙著《原色京都》中对此有叙述,这里不赘。隐元对日本最大的功绩,一是在日本开创了黄檗宗,二是将明代普及的叶茶(此前饮茶的主流是抹茶)带到了日本(日文曰“煎茶”)。隐元原本所在的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后来日趋衰败,十余年前,福清出身的实业家曹德旺等捐资五亿多元重修该寺,新寺在2019年底正式落成,我曾两次去礼拜,并在寺内住宿两晚,在经堂内讲课一次。因逸出了长崎的范围,不叙。
唐人屋敷里虽然很早就建了关帝堂并供奉了妈祖像,却并无孔庙甚至孔子像。在长崎最早创建孔庙的,倒是一位长崎的本草学家、也是医生的向井元升,他对于西洋的医学和中国的医学皆有研究,曾根据中国元代李东垣的《东垣食物本草》等撰写了《庖厨备用倭名本草》,大概由此对中国的文化心生崇敬,1647年在长崎的兴善町创建了长崎圣堂孔子庙,后来屡经变迁,到了明治初年就成了向井家的私产,1893年,在清政府的支持与长崎当局的合作以及当地华人的参与下,在今天的大浦乙三二番地建造了长崎孔庙,1905年在孔庙内创设了长崎时中小学,1967年,对原有的孔庙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形成了今天的面貌。2007年3月我去参观的孔庙,应该就是改建后的模样。闽南风的中国建筑,一对用汉白玉做成的石狮,走上石阶,正面是大成殿,悬挂的红色布帘,中间的写着“孔子庙”,两边则写着“有教无类”。黄色的琉璃瓦顶,其余为木头结构,门面、窗棂、柱子等,均涂上了令人有点眩晕的红色,一片红彤彤。两边的廊庑前,有孔子门徒的贤人石像。大成殿内有孔子的坐像,精雕细镂,金红交错,甚至是,金碧辉煌,令我感到这里供奉的似乎不是孔子,而是一位流金溢紫的帝王,全无我日常读《论语》时感受到的孔子那活泼泼的可爱相。到了后世,孔子已成了汉民族的一个僵硬的文化符号。这里现在也成了长崎提灯节的一个主会场,并设置了中国历代博物馆,时有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在此展出。
“卓袱料理”和长崎CHAPON面
2007年3月初访长崎时,邀请方长崎电视台的董事长,当晚请我们在名曰“花月”的料亭吃饭。在“花月”的前面,现在还冠上了“史迹”两个字,来夸耀其历史的悠久。它的初始,可以追溯到江户年间的1642年,距今,已有383年了。位于今天的新地中华街东北、崇福寺西面,在一个小小的台地上,抬头远远可见标示着“花月”的大灯笼,拾阶而上,脱鞋进入里面,可见长着青苔的石灯笼和锦鲤戏水的池塘,纯然的日本书院建筑,古色苍然。
江户时代,日本形成了江户、大坂(其时写作“坂”)和京都三大都市,工商业的繁荣,催生出了青楼(日语称为“游郭”)业,长崎偏隅一地,本来是没有资格与三大都市比肩的,但那时与中国和荷兰(早先还有西班牙、葡萄牙)做贸易,男人到了异地,难免要寻求女色,于是,以丸山为中心的青楼业便兴盛起来,当时与江户的吉原、大坂的新町、京都的岛原,并称日本四大花街。如今的这家“花月”的前身,是当年青楼中最高格的“引田屋”的花月楼,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了“艺娼妓解放令”,纯然的青楼瓦解了,作为高级料亭的“花月”继承了原来“引田屋”的所有地盘,成了全长崎最顶流的餐馆。
当晚,主人招待我们吃的,是“卓袱料理”。这个词从用餐方式和食物内容上,颠覆了近代以前日本人的饮食形态。这个词的内涵以及日文念法,不仅对于外国人而言是很陌生的,即便一般的现代日本人,恐怕也不熟悉。先说用餐方式。卓袱(日语发音是SHIPOKU)这个词,有学者认为是来自中国,意思是桌布(小泉和子编《ちゃぶ台の昭和》,河出书房新社,2002年),延伸义是桌子。日本在近代之前,一般没有桌子和椅子,人们都是席地而坐,吃饭的时候每人用膳(一种木制的浅浅的长方形饭盒,上置饭碗和筷子,饮酒时,置酒具),有时也用案(长方形饭盒下有四个矮脚,中文举案齐眉的案,与此大抵相当)。我在湖南省博物馆的西汉马王堆出土文物展中,看到过这样的漆器的食膳。日文称之“铭铭膳”,即每人一份的食膳,用餐时没有饭桌。由此来看,近代以前日本人的“铭铭膳”,应该也是来自中国。但中国在唐代后期,已逐渐采用西域传来的桌椅生活方式,日本恰好在此时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因而中国的桌椅方式,一直没有传入日本。
长崎的唐人屋敷,存在了一百多年,里边居住着数千的中国人,唐人屋敷建成前,更有散在长崎各处的中国人,唐人屋敷被烧毁后,又有许多中国人散居在各处。明清时的中国人,早已是桌椅的生活方式,在江户时代的画师笔下的唐人生活绘卷中,其生活状态,也与中国本土无异。这样的存在,岁月一久,自然会对周边的日本人产生影响,此外,还有长崎出岛上荷兰商馆内洋人的桌椅生活,对日本人也会有若干影响。于是,在江户晚期和明治初期,长崎诞生了一种全新的折中餐食,曰“卓袱料理”,即用餐的方式,不再是席地而坐的“铭铭膳”,而是有一个矮脚的小圆桌,食物用大碗和大盘盛放,多人共享。这样的形式,在隐元和尚创建的京都宇治的万福寺内,也出现过,当地曰“普茶料理”,不一定是矮桌,可能就是一般的方桌,只是寺院内的餐食,皆是素斋。
第二是卓袱料理的内容,与传统的和食,也有重大的差异。日本大约从8世纪的奈良时代开始,由于历代信佛的天皇的屡次下诏,禁止杀生,尤其是屠杀四条腿的动物,结果导致了直至19世纪中期的大约一千多年间,日本人基本上不吃肉,传统的和食,除了少数的飞禽(只是狩猎获得的野生的鸟类,无家禽)之外,基本上剔除了肉类。然而来到长崎的数千中国人,仍是要食用肉类的,这就出现了唐人屋敷内的鸡圈猪圈。而出岛内的荷兰人,也设法通过来自雅加达(当时称巴达维亚,爪哇岛等是荷兰的殖民地)的商船运来了活牛和其他动物,在江户中期长崎出身的画家川原庆贺所画的《兰馆绘卷》中,可以看见荷兰商馆内散养着的牛、野猪和鸡等。荷兰商馆每年还举行新年宴会,来招待相关的日本官员,在兰学家森岛中良所著的《红毛杂话》中记录了当时的菜谱,里面就有好几种肉食。这些外来的饮食,就逐渐对长崎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在一部分日本人的餐食中,悄悄地出现了肉类。于是,卓袱料理,不仅是进餐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连内容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
卓袱上,不仅有传统的蔬果和鱼类,还可频频见到肉类。今天卓袱料理的菜谱上,有一道著名的“角煮”,实际上就是猪肉的“角煮”。说起来,“角煮”是冲绳、也就是以前琉球的一道名菜。琉球在1879年被强行并入日本的版图之前,并不属于日本,日本的肉食禁令,自然不适用琉球,琉球人一直是食用肉类的,于是就诞生了“角煮”,一种类中国红烧肉的大方块状(不是上下四方形)的猪肉,特点是放入了琉球产的用稻米酿制的烧酒“泡盛”,1609年九州的萨摩藩侵略琉球后,日本与琉球两地的交流频繁起来,大概“角煮”也在一定程度上传到了九州(长崎也是九州的一部分)。
在“花月”体验的卓袱料理,还保留着当年的风味,宴会厅是榻榻米的地面,四周是格子窗户(日文写作“障子”)和隔扇(日文写作“襖”),食客围着一个漆成朱红色的矮脚圆桌,上置各色菜肴,有和式的,也有中国式的,偶尔也可感觉到一点西洋的,真可谓是和洋中的折中料理,平心而论,并不觉得好吃。进餐到一半,有几位年过五旬的日本女子来表演传统舞蹈,毕竟是上了年纪,舞姿好像也并不迷人,但这些都价格不菲,我们算是受到了隆重的招待,对我而言,比起美食的享受和舞蹈的观赏,更可贵的,是得到了一种全新的体验。
这样的卓袱料理,在长崎还有好几家,另有一家名曰“滨胜”的,也很出名,那里的餐厅,已经完全改成了现代样式,真正的桌椅,只是桌子,仍是漆成朱红色的圆桌,有浓浓的中国风。好像直到今天,卓袱料理似乎仍然还只是长崎的一个看板,其他地方极少见到。除了“桌袱料理”之外,当时还曾出现过一些极少有关中国饮食的书刊,比如《桌子烹调方》、《桌子式》和《清俗纪闻》等,但一般日本人无缘接触实际的中国料理,影响也就很有限。不过从这些书刊的名字来看,比其菜肴本身来,当时的日本人也许觉得中国人围桌吃饭更有异国风味,“桌袱料理”对日本的影响与其说是料理,倒不如说是用餐的方式,即使用桌子。而事实上传到江户和京都的桌袱料理,仅仅还留存着桌子的形式,菜肴的内容依然是传统的日本菜,当时的社会风习、食物材料以及烹调技术等,还不可能使得中国饮食以完整的形态在日本传布。
但不管怎么说,用餐桌吃饭的风习慢慢地就在都市地区传开了,人们将新出现的餐桌称为“桌袱台”,而日本的“桌袱台”实际上是矮桌,置于榻榻米之上,就餐时依然还是席地而坐,但这毕竟改变了原来的“铭铭膳”的用餐方式。需要指出的是,在江户时代,“桌袱台”的传播依然只是局限于城市的部分地区,大部分乡村地区依然沿袭了昔日的“铭铭膳”,直到明治的后期甚至昭和的前期,卓袱台才真正普及开来。
但受中国影响而诞生的另一款餐食“长崎チャンポン面”,倒是传遍了整个日本。チャンポン(发音可以用罗马字写作CHAPON),这几个字没有汉字,也不用平假名写,而是用片假名写出,用片假名写的词语大抵都是外来语,因此这个词来自海外的可能性很大。你去问日本人,チャンポン是什么意思,十有八九答不出,连店家的伙计也不知所以。但要说チャンポン面,那大抵都知道,这是一种类似于中国什锦汤面的食品,用大口的浅碗或深口的盘子盛装。チャンポン面虽说是明治以后才流行起来,但将肉和各色蔬菜炒在一起的吃法则是由来已久了,尽管经官府的多年管制,普通日本人已很少吃肉,但长崎地处西隅,当时又被幕府辟为特别的通商港,即使吃点肉食,官府也眼开眼闭了吧。チャンポン一词究竟源于何处,多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但我认为一个颇为可靠的说法是来自福建话(严格地说是闽南话)的“吃饭”,我特意请教过福建泉州的朋友,确定闽南话的吃饭,念作SHAPON,发音与CHAPON非常相像,这种面源于长崎早期的福建人,应该也可以确定了。后来,长崎最著名的中餐馆“四海楼”(长崎电视台的董事长也请我们在那里吃过饭)发布说,“长崎チャンポン面”是个他们店里的大厨、福建人陈平顺在明治中期发明的。于是,尘埃落定。
与チャンポン面很相似的,是“皿乌冬”,日本的农林水产省认定它的发祥地是长崎,“四海楼”说,也是陈平顺创想出来的,年份在1899年。这是一款チャンポン面的改良版,不是汤面,而是炒面,上面放上几乎同样的浇头,勾芡,盛放在一个盘子内,日文谓之“皿”。面条最初是与チャンポン面一样的粗面,后来又出现了细面,稍稍近似上海的“两面黄”,粗细两种并存,供食客选用。在我看来,好像都算不上好吃。
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的滥觞——长崎的“唐通事”
17世纪初来到长崎一带的中国商人,几乎全都不会说日语。不过,在唐人屋敷还没有设定之前,也就是中国人可以自由行动的年代,已有一小部分人在长崎定居下来了,且几乎都是娶当地的日本女子为妻,在日本生儿育女,日后也渐渐融入了日本社会,甚至有改为日本人姓的。日积月累,他们也就慢慢学会了当地的日本话,至少,他们的子孙,第一语言几乎都成了日语,也许由于上一代的坚持,在家里大都还使用中国话。于是,他们就成了中国商人与当地贸易部门或日本商人之间的中介,后来慢慢衍生出了“唐通事”这样一种既担任译员又实际担当贸易业务的官职。“通事”一词,源于中国,古时有多种含义,其一为移译,南宋时周密所撰的《癸辛杂识二集•译者》中说:“译,陈也;陈说内外之言皆立此传语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谓之通事。”这一意义的“通事”一词,也较早地传入了日本,720年问世的《日本书纪》卷第二十二中就已出现,记载小野妹子出使唐(实际上应为“隋”)时,“以安作福利为通事”,即那时东亚间的国际交流,已有随行的口译,完稿于901年的编年体正史《日本三代实录》中,也有大唐通事某某、渤海(698-926年存在于现中国东北地区的国家)通事某某等的记载,成书于927年的法令集《延喜式》中,有“大唐通事”、“渤海通事”、“百济通事”、“大通事、少通事、小通事”等的词条,其意义仍在于国际交流中的语言传达。至今日语中的口语翻译仍写作“通译”,显然是这一流脉的体现。为了区别中文翻译的“唐通事”,江户时代将与荷兰人进行沟通和贸易的官员称为“蘭通词”,简称“通事”、“通词”,两者的日语发音一样。
长崎的通事制度,起源于1604年(江户幕府建立的翌年),当时长崎奉行(奉行为官职名,一般指各行政部门的最高长官)任命生活在长崎的中国人冯六(后改为日本姓氏平野)担任通事,这一制度或者说这一官职一直延续到江户幕府垮台的1867年为止,共有263年的历史。通事的制度,到了1653年完全成熟定型,正式的通事一般由9名组成,分别是唐大通事5名,唐小通事4名,另设稽古通事11名。“稽古”一词,原为稽考古道之意,在《尚书》、《后汉书》等已有出现,但使用似乎并不普遍,传到日本去,就衍生出了技艺、艺道等领域内的学习之意,这里的稽古通事,可理解为见习翻译吧。大通事地位最高,小通事次之,稽古通事则有点候补通事的意思。这一类的通事,又称为“本通事”,就是真正担当翻译和贸易事务的,地位相对比较高,此外还有一类被称为“内通事”,会一点中国话,主要从事中国商人的生活安排、具体事务的跑腿、货物的装运等,人数较多,在170人左右,有点类似通事里的杂役。不过内通事也有些水准相当不错的人,比如1719年出版的江户时代最早的中国语教本《唐话纂要》,就是由内通事冈岛冠山编著的。本通事大多由华人或是华人的后裔担任,内通事大多由当地的日本人担当。
但是,当时所谓的中国话,其实并不统一,在明末和清代,来到日本做贸易的,大致有三个语言体系,即来自福建的福州话和漳州话(也可理解为闽南话),以及长江下游两岸的南京官话。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时,定都南京,在14世纪末期至15世纪前期展开的日明勘合贸易,中国的主要口岸城市是宁波(之前曰明州,因避明讳而改名宁波),长江下游一带,也是方言众多,彼此沟通的主要语言是南京官话。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日本一直把南京作为中国的指称,这一时期来自中国的物品,很多被称作“南京某”,诸如“南京兔”、“南京梅”(腊梅)、“南京虫”(臭虫)等等,甚至中国人,也曾被称为南京人,乃至明治时期,这一情形依然在延续,比如这一时期在日本的华人集聚区,也被称为“南京町”,早期的横滨和神户的唐人街,都被叫做“南京町”,横滨的后来改为“中华街”,但是神户的依然故我,一直用到今天。因此,在江户时代,南京也成了中国的指代词。南京官话,在日本和当时的琉球,都曾有一些会话课本留下来,以此来看,似乎与现今的普通话,差异也不大,但是发音如何,却是难以考究,我的估计,大概是一种南京周边(包括南京、镇江、扬州和临近长江的安徽话等)各种北方语系话语的杂糅。曾担任过唐通事、后来在明治时期的外交舞台上甚为活跃的郑永宁,1880年在“兴亚会”的一次集会上,对于南京官话发表过这样的见解:
(南京)官话是明末清初南方所使用的一种通用语。南人不屑于讲北话。北人亦对此无可如何。元人在燕建都以来,宋代之遗臣无法忘却浙杭。明成祖在燕建都以来,太祖(朱元璋)之遗臣不忍离开江苏。更何况满清革鼎之后呢!(《東亜会報告》第四集,1880年5月14日。此处译自中嶋幹起《唐通事の担った初期中国語教育――南京官話から北京官話へ》,载《東京外国語大学史》,1999年,第875页)
这里强调的是前朝遗臣对南方故土的留恋,即便是官话,也依然留存了江浙一带的口音。
至于漳州话与福州话,虽同在福建,却并不相通,与两地之外的其他语系也不通,因此在1661年设立的大小9名通事中,漳州话、福州话、南京官话各占三分之一,以应对来自不同地域的商人,但到了后来,南京官话占了上风,甚至在17世纪前期还有来自吕宋(今菲律宾)、暹罗(今泰国)、东京(今越南北部)等地的商人,彼此通用的语言,据说也是以南京官话居多。
1639年,江户幕府彻底完成了锁国的政策,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主要是华人),一旦回国之后,就不可再自由地居住在日本,这就迫使当地的华人或者永久归国,或者皈依日本,于是,就在长崎一地形成了世代定居的华人。那么,久居日本之后,如何保障华人的后裔南京官话这一语言或语文的脉络得以代代传承,尤其是还要担当与中国商人进行沟通的通事呢?这就需要专门的学习了。当时的长崎通事中,形成了比较有影响的林家、郑家、叶(后改日本姓“颍川”)家等几个家族,他们为了让自己的后裔继承通事的家业,就开办了若干学习中国话(主要是南京官话)的家塾(一般称为“译家学校”),除了自己的子弟外,也招收外来人员。起始的年龄,一般在7-8岁,学习的教材,开始时是用南京官话(当时一般称“唐话”)的发音熟读乃至背诵诸如《三字经》、《大学》、《论语》、《孟子》等,有点类似中国本土的私塾学习,这大概主要是语音的训练。因为熟读了这些经典后并不能解决日常的口语,尤其是贸易船的业务会话,于是接下来还有他们自己编的《译家词长短话》、《译家必备》等,集中编纂了一些两个字(诸如“恭喜、多谢、请坐”等)、三个字(诸如“不晓得、吃茶去”等)和四个字的日常词语,还有一些《译家必备》、《养儿子》、《闹里闹》、《二才子》等比较浅显的口语读物,这一类自编的教材,在长崎的图书文献馆等还藏有20余种。再进而跟着老师习读《今古奇观》、《三国志》(应为《三国演义》吧)、《水浒传》、《西厢记》等明清时期的通俗小说、剧本等。程度深的,还可跟着老师阅读《资治新书》、《红楼梦》等作品。
由此可见,这些私塾重点培养的是学生的口语沟通能力和一般的书面阅读能力,汉学的修养在其次。此外还需掌握一些他们自己编纂的航船、贸易物品名、装卸起运、价格谈判等的词语和说法。最后根据其语言能力、实际经验、运作能力等综合因素,来判定其在通事中的角色和地位。
这些通事的行事范围,也只是局限于长崎一地而已。明清时期,中国的海禁政策,时紧时弛,行至长崎的商船,也是时多时少。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主导权,渐渐转移至欧美人手中,1854年日本被迫打开国门后,尤其是1858年先后与英国、法国、美国、俄国、荷兰等国签署了通商条约之后,日本的外贸对象国,也从中国转向了欧美诸国,对外开放的港口,也扩展到了横滨、神户、大阪等地。如此一来,长崎港的海外贸易地位,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业务,明显出现了下降。原来以唐通事为业的人,尤其是这一带有祖传世袭色彩的职业,面临了危机。1867年7月,唐通事的官职和制度取消了。然而日本锁国时代的结束,也给这些唐通事带来了新的机会。早在幕府时期的1862年,即派遣了官方的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据记载,也有两名唐小通事(也有写作通词的)同行,即便是小通事,依然属于官员,通事之下各有一名跟班的随员,可见其地位的不低。
日本国门打开后,除了要培养通晓西洋语文的人才外,中国语也未被忽视。1871年2月外务省设立了汉语学所,是近代日本官方设立的第一家学习口语体汉语(而非汉文)的教育机构,这也表明,以前一直作为中国语指代词的“唐话”,现已由官方正式改定为“汉语”。汉语学所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掌握汉语、与中国展开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的译员,初步的计划是在日本学习两年,然后再派往中国本土深造。招收的学员年龄,在11-13岁之间,也有比较年长的。当时正值日本文明开化之风炽盛的年代,中国的形象已在日本渐趋下降,原意来学习汉语的日本人甚为寥寥,因而学员的来源,大部分竟是唐通事的子弟(亦即华人的后裔),即便如此,60人的定员,也未必能够招满。
而汉语学所的教员,几乎清一色来自唐通事,开办之初,共有教员9人,分别是:督长(负责人)郑永宁;督长兼教授叶重宽(日本姓氏颍川);叶雅文(日本姓氏颍川);蔡祐良;源通义(日本姓氏诸冈);周道隆;张武雅(日本姓氏清河);刘中平(日本姓氏彭城);藤原肃之。只有最后一位似乎是日本人,其他应该都是华裔。
所用的教材,也完全沿袭了唐通事学塾时代的教科书,为《汉语跬步》、《二才子》、《闹里闹》、《译家必备》。《汉语跬步》,主要根据类别,列出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的常用词语。比如两个字的部分,分为“天部”、“地部”、“人部”等,在“天部”中,列出了“天地”、“乾坤”、“天河”、“天阴”、“起雾”等词语。整个教学,没有系统的语法和句型的讲解训练。词语或句子的发音,也是唐通事时代通用的南京官话。差不多可以说,外务省的汉语学所,几乎就是长崎培养唐通事的学塾的延续或翻版,只是所有的经费,均由官方支出。
外务省的汉语学所,从教学制度到教学方法、教材乃至教员和学生,与江户时代长崎的唐通事学塾并无大的差异,但是它具有此前唐通事学塾所完全没有的两点重要意义,第一这是一所国家设立的学校,代表了国家对于汉语教育的重视,而不是当年华人的后裔为了延承世袭的家业;第二其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外交外贸人才,而不是培育地方上的人士谋求生计的手段。它将汉语教育的位阶,从地方上的私域,提升到了整个国家的公域,将汉语教育和汉语人才的培养,收纳到了整个国家对外发展的视野和方针中。这是在明治国家刚刚建立不久、财政较为拮据的状态下不惜每月拨付两千两银两来兴办外务省汉语学所的根本意义所在。
长崎在日本的最西隅,而中国又在长崎之西,中国自然是东方文化或是东洋文化最主要的发祥地和兴盛地,对于长崎或是整个日本而言,这东洋风,则是从西边吹来的。
作者:访客本文地址:https://www.zsclv.com/zsclv/13685.html发布于 2025-07-05 10:31:47
文章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处中首车旅集团